60年教育纪事:科学春天里的少年突击(2)

王永与谢彦波、徐建军、胡天跃在寝室里。(资料图片)
少年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在那个百废待兴、知识荒芜的年代,需要一个、一批甚至更多的知识英雄来唤醒国人对知识的渴求,对科学的重视,少年班就扮演了这样一个“突击兵”的角色。
1978年,各大报刊刊登了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围棋的照片,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指点星象的样子,也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他的故事甚至成了手抄本题材,广为流传,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不仅仅是宁铂,少年班其他的孩子也频频出现在报刊上和纪录片的镜头中。神童们的故事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孩子,少年班也成为了这些孩子心目中神圣的科学殿堂。
1977年,14岁的王永还是一名初三的学生。秋季的一天,王永偶然间从父母那里听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紧紧封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将重新向青年学生敞开!
1978年,这个9岁才开始上小学,但连连跳级的聪明孩子在偶然间看到了另一个聪明孩子的故事:宁铂——一位13岁的天才少年,刚刚被中科大录取。“我是从媒体上知道宁铂的,当时对他的宣传已经铺天盖地了。我觉得他们这些人都很神,也觉得自己好像跟他们的差距非常大。”王永向记者回忆说。
然而此刻,少年的心犹如被打破了平静的湖面,王永很快便作出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也要上大学,而且也要上中科大。
几个月后,当时还上高一的王永以惊人的速度学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与其他610万名考生一起,走进了1978年的高考考场。
“高考我考了全县第一名,第一志愿我填报的就是中科大。”王永说,当时自己根本没有想到会上少年班,直到接到长丰县教育局要他去合肥四中参加少年班的选拔考试时,他也并不认为自己会考取。
“少年班的招生考试也经过了好几关:初试、笔试,然后再口试。现在回想起来,口试时老师问的题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奥数题,很难。”当时,这个来自长丰县的少年根本没见过这种题型,不过幸运的是,他全部答对了。“老师当场决定录取我为少年班学生。”王永说。
“作为少年大学生,走在大街上都会有一种优越感。”少年班第二期学员、中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周逸峰回忆说,他被少年班录取的消息在县广播台连续播了一个星期,“寒暑假回家,县委书记、县长都会到我家来探望,了解我的学习生活情况,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
中科大少年班管理委员会原主任肖臣国说:“很多少年班学生进校后,我们问他们,你为什么要考少年班,不少人都回答,因为看到宁铂这么小就能上大学,所以我也要上大学。”
10月,王永、周逸峰等67名智力超常的少年进入了科大少年班,与宁铂等首批21位少年一起,一共88个孩子,同属首届少年班。从此,这88个孩子就与“少年班”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开始接受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常教育实践。
少年班第一期学生、IEEE会士、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姚新说:“刚来的时候,中科大就从物理系、数学系抽调了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课,而且还经常安排我们和一些知名的科学家见面,所以无形中就给我们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激励。虽然年纪小,可我们心里很明白,整个学校、整个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值都比较高。”
由于一进校就被罩上了“天才少年”的耀眼光环,少年班学生“大学语文”上的第一课就是王安石的《伤仲永》。课后,一个学生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警惕着!泯然众人矣。”当时少年班里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骄傲的尾巴按下去”。
在一部分人眼里,天才似乎该是那种整天玩耍却能不费吹灰之力解决常人难以解决的问题的“超人”。王永说:“少年班的同学对待学习都特别认真,肯花功夫。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法。至于我嘛,我的课堂笔记可能是比较有特色的。老师说一句我就记一句,有时甚至还记录一些老师的即兴语言或动作,可以说我的笔记是‘现场直播’式的。不仅如此,课后我还会找时间把这份笔记再整理一遍,因为当堂记的比较潦草凌乱,我会把它们誊到另一个本子上,一边誊写,一边回忆一下老师讲课时的情景,像放‘实况录像’一样。这样,我上课的时候为了尽量记得详细完整,肯定会全神贯注,而课后再整理,相当于学了两遍,效果自然很好。”
从1983年起就担任少年班班主任的叶国华,对上个世纪80年代那帮孩子们的刻苦劲儿一直记忆犹新:“每晚10点半左右,我都要去少年班宿舍区,抓孩子们回去睡觉。那时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寝室晚上关灯后,孩子们有的跑到路灯下去看书,有的抱上被子到教室里去学习,整晚都不回来。好多学生都抱定一个心思——将来我要当科学家。”
与普通大学生一样,少年班的孩子们也是戴着校徽出入图书馆和实验室,住7个人一间的宿舍,吃5分钱或者1角钱的饭菜。
除了学习外,踢球、玩耍、练习武术、听音乐、下围棋是他们最喜欢的事。然而,班上大多数学生的年龄太小,班主任汪惠迪便承担起了老师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在早上帮他们冲奶粉,有时还要为每人煮上一个鸡蛋。除了白天的文化课之外,下午她还要给他们加上一节当时学校里还没有开的体育课。晚上她要去查房,替他们关灯。
“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一袋奶粉,就在少年班,汪老师送我的,说是让我注意营养。我平生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礼物,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表达,只记得自己好像很乖很乖地点了点头。”在少年班第2期学生吴向东的记忆中,汪老师是他见过的最好的老师,“她以一种本能的母爱温暖着我们,像妈妈一样关心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少年班的孩子们在学校和老师的呵护下成长着,但不可避免地,他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用‘天才’、‘神童’,甚至‘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的头衔对这些早慧少年进行‘轰炸’,影响了这些孩子的成长。”尹鸿钧表示。
1985年,在媒体的过分渲染下,使得宁铂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神童’的称号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除了宁铂,少年班年纪最小的学生谢彦波也始终是媒体追逐的对象。有媒体甚至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当他跨进大学校门时,他还带来了自己心爱的玩具——一只铁环。“谢彦波滚铁环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后,铁环就一直静静放在寝室,谢彦波很少再去碰它了。即使是偶尔拿出来玩,也觉得不是很开心的事了。”与谢彦波住同一个宿舍的王永说。
“后来,我们逐渐意识到,少年班的学生受舆论影响太大了,必须引起关注。”叶国华说,从1985年起,中科大规定,任何媒体不得采访在校少年班学生。宁铂现象让学校开始注重学生的心理教育。1982年,从安徽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孔燕成了少年班第一任心理辅导员,以后每届少年班都配备了专门的心理辅导员。
“其实,少年班学生并不是只会数理化的木讷‘天才’,也不是高智商低情商的懵懂孩童。他们爱好广泛,活泼开朗,是个单纯、快乐、充满朝气的群体。”孔燕告诉记者,少年班学生不仅专业课学习成绩优异,在国内外各种科技竞赛中频频获奖之外,在文体活动方面表现也非常突出,在校合唱比赛、辩论赛、足球赛、围棋赛等文体赛事中屡屡夺冠。少年班首期学生江凤至今仍是中科大女子跳高纪录的保持者。2001级学生胡波本科期间曾在《物理评论快报》发表论文,他同时也是学校“树之”演艺社的社长、“中科大学生艺术团”曲艺团团长。
相关文章
- 教育部:公办学校不得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建校费
- 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中小学上好“开学第一课”
- 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教师网文掀网友热议
- 洛阳教育局长公开“晒廉” 两年免职4名校长
- 央视揭强售教辅材料乱象:地方教育部门成主体
- 成都青羊区教育局官员因微博调情大胸女被免职
- 湖南教育厅:称乱收费1万不算大事官员系外聘者
- 教辅乱象背后利益链揭秘:教育局和学校分享利润
- 教育部:中小学生身体素质连降局面得到遏制
-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谈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目标
- 海南教育厅发文规定统一中小学校服被质疑卖校服
- 高等教育公平研究: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持续滑落
- 教育部征集乡村教师照片号召网民写微博谢师恩
- 教育部: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 农村孩子大批进城就学 城乡教育失衡难题待解
- 教育部在六地区开展中小学校车运营管理试点工作
- 零容忍:教育部全国通报6省12所乱收费中小学
- “富二代”成为特殊群体 教育该如何下手?
- 教育局要求中小学老师布置学生作业前自己先做一遍
- 教育部官员谈汉语能力测试 称有助复兴母语文化
推荐内容
教育新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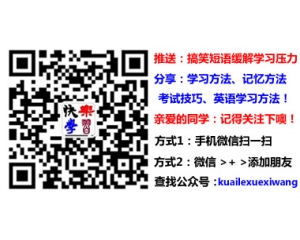 自学习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自学习网官方微信公众号 灾区又闻读书声
灾区又闻读书声 灾民安置点的“儿童乐园
灾民安置点的“儿童乐园 做“低碳小公民” 迎“
做“低碳小公民” 迎“